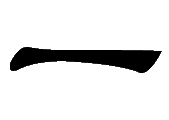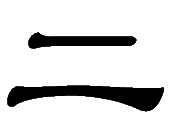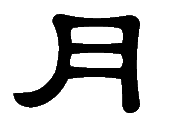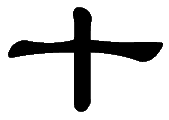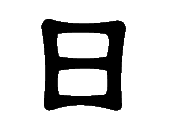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万吨钢呀呵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花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运到操场上自搭的土高炉去烧。我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锯了多可惜,放在这炉里能炼出钢铁么?老师把眼一瞪:“想偷懒是吧,听党号召没错”。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老师来问我他同我说了什么,我如实回答了,想不到的是为此事竟开了批判会,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当时,我站在批判会上低着头涨红着热辣辣的脸,嗫嚅着如实说了一遍他同我说的话,那情景犹如我自己在挨批判。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临初中毕业离校前夕,我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兜一圈时,发现一个杂物间里堆着当年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锈渍斑驳的一堆烂铁,旁边散乱着依稀可辨的“15年赶超英国”等横幅。“听党号召没错”?想起老师的训诫,又联想起我愧对的那个右派好人和终生卧床的残废同学,连串的问号始终困扰着我的少年时代。
90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节选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眼里的共产党与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