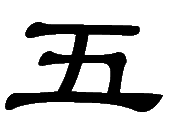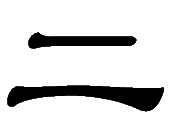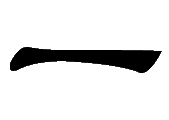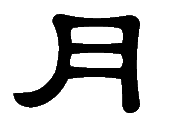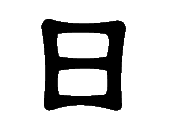(大陆来稿) 我今年八十八岁,离休干部,在省城住着宽敞明亮的厅长楼,月薪不菲。可最近几年,家人连遭不幸:儿子、老伴、二女儿患癌症手术,独生孙女离异,老伴离世。垂暮之年的我,悲伤
而无奈。但偶尔也有高兴事,如老友来访,涨工资等。特别是每年新年前夕,我姐姐的两个儿子都会来拜年。
姐和我出身于书香世家。姐姐自幼聪慧善良,姐夫是个教书先生,土改时因姐夫家有十几亩地,雇了一个长工,被划为“地主成份”。姐姐头顶“五类分子”的帽子,饱受屈辱,家里穷得叮当响。
那时,我和丈夫在省直机关任职,为自保而免受牵累,对姐姐家不曾援手,连她家的门都没踩过,偶尔回复家信,为怕被人拆看抓了把柄,末尾总要加一句教育姐姐:“老实认罪守法,别乱说乱动。”
后来,姐姐家二子三女陆续都进了城,有的大学毕业当了干部,有的做生意成为富商。特别是,大姐的几个子女都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身体健康,为人真诚、和善、厚道,亲邻多有美誉。
姐夫、姐姐辞世后,几个晚辈对我们老俩口非但没冷淡,反而敬重有加。
外甥女经常打电话问候;我家有重要事儿,外甥不请自到;每逢过年,两个外甥都会带着当地土特产,驱车数百里前来拜早年。在每一次暂短相聚的交谈中,外甥那朴实的话语,恰似寒冬里的缕缕春风,温暖着我们的心。
外甥女经常打电话问候;我家有重要事儿,外甥不请自到;每逢过年,两个外甥都会带着当地土特产,驱车数百里前来拜早年。在每一次暂短相聚的交谈中,外甥那朴实的话语,恰似寒冬里的缕缕春风,温暖着我们的心。
每当送走外甥后,我们老俩口照例会议论一番。老伴喜读书,粗通文墨,感慨说:“外甥所为,可谓古风犹存,以德报怨!他们说话谦卑,有见识,有内涵,与当今那些浅薄浮躁的‘暴发户’,不可同日而语。”
我说:“我也有同感!现在的人,金钱至上,人情比纸薄。修炼人,就是不一样。看起来,电视、报纸的宣传不可轻信,法轮大法是很不错的!”
2016年7月,我老伴病故。老伴虽然是以高寿辞世,可六十多年的风雨同舟,一朝永别,仍令我痛惜不已。离年关越近,我越感失落孤寂。
腊月二十以后,天气不佳,一连几天都是雨夹雪。我自忖,今年外甥可能不来了。腊月二十六下午一点多,我刚想躺下午休,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外甥来了。
风雪天,佳节里,孤寂之中,看到远道而来的亲人,我泪眼婆娑。
饭后聊天,我对外甥说:“冰天雪地的,家里那么忙,路那么远,你们还来看我,令我于心不安。”大外甥说:“作为晚辈,尽孝道是本份,我们应该来。您与我娘是一奶同胞的亲骨肉,姨娘姨娘,姨就等于娘,我娘不在了,您老人家就是我们的娘。”
二外甥说:“家有老,是一宝。如今,我们两家几十口,仅有您这一宝了,当然更珍贵!姨父刚走几个月,又赶上年关,您老人家心里会不好受,我们来拜年,见见面,您老人家心情会好一些。所以,今年我们更得来。”
外甥的话,我听着心里暖暖的,同时,也有隐隐的愧疚。就借机问他们:“孩子,在你家最困难的那些年,姨没帮助过,你们真的不怨恨吗?”二外甥回答:“姨,说实话,对于您和姨父,我们曾经自豪过,也曾经沮丧过。自豪的是,我们家有一门当‘高官’的亲戚;沮丧的是,这门官亲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大外甥微微一笑,说:“自豪也罢,沮丧也罢,那都是在我们炼功之前。自从修大法以后,那些狭隘自私的情绪,很快就随风飘散了。师父教我们要慈悲宽容,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们想象过,当时,您身上贴着娘家‘成份不好’的标签,在‘唯成份论’政治运动的高压下,如履薄冰,肯定没少受委屈。您对娘家人的冷漠疏远,所谓的‘划清界限’肯定是违心的。说到底,那是因为政策邪恶。自从炼功以后,对于您,我们真的是理解了!”
听着外甥的话,遥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不免一阵痛心酸楚。晚辈的理解和体谅,打开了我多年的心结,身体从里到外的轻松。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腊月,外甥又该来拜年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愉悦地回味着,期待着。
托大法之福,我方能受到外甥们如此礼遇。我应该感谢大法,感谢给天下送福的李大师。为表寸心,特借明慧一角致谢,给李大师拜个早年,恭祝大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