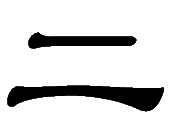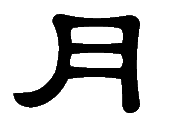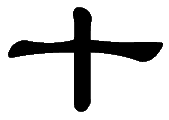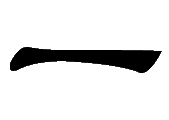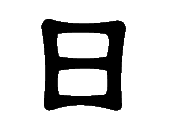(大陸來稿)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們全家一起看電視。中共電視臺突然播放「天安門突發自焚事件」,當看到燒傷人員全部被包紮的鏡頭時,我頓時明白這是假的。因為我曾親眼見過並護理過嚴重燒傷的人。
護理被燒傷的同事
一九六八年盛夏時節,由於大面積的「武鬥」,全國各地基本處於癱瘓狀態,一到晚上一片漆黑。
某天晚上八點多,我單位計量室一位二十三歲的女工,帶著同寢室兩個室友到計量室倒煤油。因為看不清、錯倒了汽油,在點燃火柴的一瞬間引發汽油燃燒,爆發一場火災。三個人中,離門口近的一個在慌亂中逃出;另外兩人被救出來後,一個中度燒傷;一個嚴重燒傷。
重度燒傷者當時十九歲,與我在一個車間、一個小組上班。因為大面積停電,醫院也沒電。車間領導選派了三個與她同齡的少女和兩位年齡較大的師傅二十四小時輪換在醫院守候,我是其中一員。
當時醫院的條件都很差,一個大病室擺了十張床。所謂的搶救也不過就是掛上吊針而已。我們三個女孩的任務就是不間斷地、在她燒傷的地方輕輕地塗抹紫藥水。病人一直處於昏迷狀態,她一絲不掛地平躺在床上,我們用一塊布遮住她的隱私部位。
我們三人八小時一換班,在這期間一點不敢疏忽,她被燒最嚴重的部位是整個面部、兩隻胳膊和雙手。我們不停地用棉簽蘸紫藥水,輕輕的塗抹,以免燒傷處流水,否則引發感染就會危及生命。在我們認真、小心的護理下,在那麼簡陋的醫療環境中,她竟然度過危險期、僥倖活下來了,真是萬幸!
如今她已七十三歲了,儘管她的面部、雙臂、雙手一直疤痕累累,但她畢竟活著,而且兒孫滿堂。
看望被燒傷的孕婦
大概是一九八六年盛夏的某一天,廠保衛科兩個員工在辦公室用汽油清洗武器,當時基建科長坐在旁邊抽煙,一不小心煙頭掉進汽油盤裡。瞬間盤內汽油燃燒起來。慌亂之中,其中一人端起火盤扔出門外。誰也沒有想到,此時此刻、其中一位員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來找他,燃燒的汽油不偏不倚、全部倒在這位已有數月身孕的少婦身上。
據當時院內其他目擊者講:真是慘不忍睹,她倒在地上滿地打滾,滅火器好不容易把她身上的火滅盡,因化纖衣服燃燒後黏在身上,所以傷勢嚴重。
兩日後我和幾個同事去醫院探望,在醫院一間單獨封閉的小房間裡,我們從窗外看到:一張手術床上躺著燒傷的、一絲不掛昏迷不醒的病人,在她身上罩著玻璃罩。據說要讓她身體保持乾燥、無菌,不流水。我想,現在的醫療條件與十八年前簡直不能比。我們期待著她的康復,母子平安。然而事與願違,醫院沒有把她救活。一屍兩命哪,至今回想當年還是感到難過、痛惜之極。
當我看到中央電視臺(CCTV)上播放的「天安門自焚」燒傷人員全部被包紮的鏡頭時,當即告誡全家人:「這是假的,你們看這些『自焚』的人,個個包得像粽子一樣,全身纏滿繃帶,人被燒傷後會起泡、流水,那些繃帶不都黏在皮膚上?拆繃帶時連皮都會扯下來,這些人不都成了骷髏,能活嗎?你們千萬別相信。」全家人都沒有反駁。大面積深度燒傷不宜包紮,這是基本常識。
與四個老太太的對話
大概十年前,某天散步遇到四個老太太在一起聊天,她們聽信了自焚謊言對法輪功頗有微詞。我坐下來問她們:「老大姐們,在家裏做飯炒菜嗎?」
她們回答:「做了大半輩子了。」
我又問:「胳膊、手、被燙到、燒傷到過沒?」
「那是常有的事兒。」她們說。
我問:「疼嗎?」
她們答道:「疼得很,用冷水沖,用醋澆都還疼。」
我又問:「你們都看了電視上放的天安門「自焚」,那個身上燒得亂七八糟的人咋就不疼呢?他應該疼得滿地打滾才對呀。」
她們有所醒悟,說:「是呀,真的呀。那咋回事呢?」
我告訴她們: 「老姐姐、那是演員演出來的,栽贓嫁禍法輪功的。你們都經歷過文革,那不是為了煽動仇恨、叫大家都參與整人的運動嗎?千萬別忘了文革的教訓,再次被利用啊。」
接著,我把一個個疑點分析給她們聽,她們都明白了。
二十餘年來,天安門「自焚」偽案毒害了多少人?!特別是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那時我的小孫子才上學,拿回來的課本上都有「自焚」偽案。我說把這些騙人的內容撕下來,孫子非常贊成。二十多年了,還有多少人沒有清醒過來?
希望藉此機會喚醒那些被兒時課本上欺世謊言毒害的孩子們,使他們都能明白過來, 遠離邪魔,平安度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