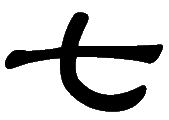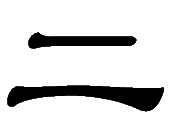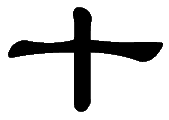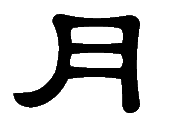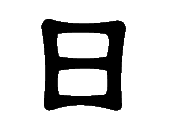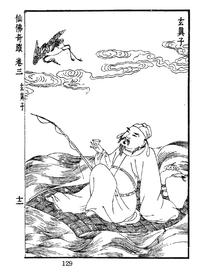有關「白日飛升」、懸浮、起空,在東西方的文獻記錄中都有大量的記述。比如印度的瑜珈師、隱士與行者中,都不乏能夠起空漂浮者;西方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飛行修士」的記載。在普遍敬佛修佛的民族和地區對這類超常現象也沒有抵觸。古今中外都有眾多的目擊者記錄,以下是幾個例子:
【接上期本版】
三、史書中更多對「白日飛升」的記載
1. 黃帝乘龍而去
對於「白日飛升」,最早的記錄見於《史記﹒孝武本紀》描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珣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大意為,黃帝用首山開採出來的銅在荊山之下鑄鼎。鼎鑄就之時,有黃龍從天上飛來,龍鬚飄飄,請黃帝上背。黃帝騎了上去。妃嬪群臣們也跟著上去,有七十餘人。其他上不去的只好扯著龍的鬍子。可惜凡心太重,龍鬚斷裂,黃帝的弓也隨之墜落,眾人也掉了下去,眼睜睜看著黃帝離去,抱著龍鬚與弓哭倒在塵埃中。後來這個地方就叫做鼎湖,現在位於河南省靈寶市。黃帝墜落的弓被稱為烏號。
對於《史記》的信史價值,歷來為學術界認可。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對於上古的事,博採各種史料,對於難以把握的就放棄,比如,他讀到記述上古年譜《歷譜諜》(已佚失)的時候,由於「古文咸不同,乖異」,他就棄之不要了。司馬遷對於黃帝「白日飛升」雖然只是簡單交待、春秋筆法,但是對於史家來說,沒有被眼見為實的侷限性所束縛,是難能可貴的。
在《二十四史》正史中,主旨在於以禮治天下,以德序人倫,所以並沒有大量記錄「白日飛升」等修煉界的事例,但是在官方主導的類書中,卻有大量的記錄。在宋代「奉敕撰集」的《太平廣記》中收錄了大量的修者「飛升」、「羽化」、「屍解」等事例。
2.張志和當著顏真卿等人的面飛升而去
《太平廣記》中有一例是說唐朝大詩人張志和的修煉事蹟,人們熟知他的詩作,但實際上他還是一位得道的修煉人。
張志和,是會稽山陰人,博學多才,文采超然,考中了進士。他不僅詩才甚佳,還善於書畫。張志和修煉的情況在《續仙傳》中有零星的披露,說他是個「守真養氣」的人,可以「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的山水都為他所遊覽,對於功名他早已淡然。
魯國公顏真卿和他是好朋友。顏真卿在湖州任刺史時,與文人志士一起喝酒,席間一唱一和地作《漁父》詞,那頭一首就是張志和的詞。詞是:「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顏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一共和了二十五首,互相傳遞著誇賞。張志和讓拿出來顏料和剪裁白絹,畫《景天》詞的詞意,不一會兒就畫出來五幅。花鳥魚蟲,山水景象,筆法奇絕,今古無超。顏真卿和客人們傳著玩賞,讚不絕口。後來顏真卿東遊平望驛,張志和喝酒喝到酣暢時,作水上遊戲,把坐席鋪在水面上,獨自坐在上面飲笑吟唱。那坐席的來去快慢,就像撐船的聲音。接著又有雲鶴跟隨在他的頭頂上。顏真卿等在岸上觀看的人們,沒有不驚異的。不多時,張志和在水上揮手,向顏真卿表示謝意,然後便上升飛去。
3.顏真卿屍解而去
「白日飛升」是修煉者圓滿離開人間時的超常形式之一,而屍解則是修道圓滿時所用的另一種常見方式。
顏真卿開創的顏體楷書「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博大精深、雄逸豪邁」,「心通古意、寓巧於拙」,在中國書法史上影響巨大。他早期書寫的《多寶塔碑》(全稱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中期書寫的《東方畫讚》、《顏勤禮碑》、晚年的《麻姑仙壇記》等,既是書法佳作,又折射出他個人的修為歷程。
《太平廣記》中也收錄了唐朝著名書法家,太子太師、魯郡公顏真卿勇赴叛軍大營,寧死不屈,英勇就義的事蹟。此外,《太平廣記卷三十二》還記載了:顏真卿死後十餘年,顏家的僕人曾遇真卿於洛邑。顏真卿說,「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意思是,我曾經是修道之人,要保全的身體完整。顏真卿即是以「屍解」的方式圓滿。屍解的常見形式是,得道圓滿之人,先任常人入棺、下葬,之後化出一根竹竿或一隻鞋子留在棺內,自己則以得道之身、生前相貌繼續在世間做度化有緣之事,同時也能出入仙界。
在歷史上的歷朝歷代,修煉文化以不同形式呈現,但表現的都是修煉提升、回歸天界。從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逐漸開始興起的氣功熱,特異功能熱,反映的正是人們內心深處對於返本歸真、嚮往永恆的渴望。神傳文化造就了以道德為本的做人和修為基準,所以中國人骨子裏其實都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文化根基。
(待續)